兼议划分市场份额垄断协议行为的认定
本案是一起较为典型的垄断协议案件,由于当事人先后提起多次行政复议和诉讼,使得本案受到了学界和媒体的密切关注。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争议焦点是当事人的业务收入统筹和再分配行为是否构成《反垄断法》规定的“分割销售市场”。对此,当事人认为对收入的分配不能导致销售市场被瓜分。而笔者则认为,对收入的人为分配属于划分市场份额,而划分市场份额正是垄断协议行为中“分割销售市场”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此稍作探讨。
“划分市场份额”属于《反垄断法》规定的“分割销售市场”行为
《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明确将“分割销售市场或原材料采购市场”作为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的垄断协议的一种形式。在《反垄断法》中,“分割市场”的垄断协议表现形式有多种,常见的有划分地域市场、划分交易对象、划分产品类型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表现形式是划分市场份额,是指经营者之间对彼此的市场份额作出约定,从而避免彼此之间激烈的竞争,维护垄断协议成员的共同利益。市场份额通常是该经营者的市场销售量在市场同类产品中所占的比重,其评价指标有多种,如经营者销售商品的件数,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收入等,对互联网企业还可以根据用户对其访问量等指标进行计算。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虽然未明确将划分市场份额作为分割市场垄断协议的一种表现形式列举,不过通常可以将第五条第(一)项“划分商品销售地域、销售对象或者销售商品的种类、数量”中的“划分商品数量”作广义理解。正如《反垄断法》中的“商品”不能仅理解为有形的物的商品,也包括服务,商品的数量也不应狭义地理解为有形商品的数量。对于服务来说,通常无法以个数来计算其数量,因此市场份额(通常也表现为业务收入)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商品数量的一种计算方式。
划分市场份额的垄断案件较早出现在欧洲,1992年欧共体委员会对海上班轮运输企业之间的市场分割协议进行了处罚,参与同盟的企业对法国和11个西非和中非国家之间的商品运输服务市场份额进行了分配,超过市场份额的货物只能交由同盟其他成员进行运输。
自2008年《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工商机关查办的多起垄断协议案件,如2013年湖南省工商局查办的一系列保险行业垄断协议案以及2015年江西省工商局查办的保险公司垄断协议案,都属于此类划分市场份额的垄断协议案件。
当事人的“业务收入统筹和再分配行为”本质上属于对市场份额的划分
本案与传统的划分市场份额行为的一点区别在于,传统的划分市场份额行为通常是事前划分,而本案中的收入统筹是在事后,这也是当事人据理力争的一点。然而,分析垄断行为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划分市场份额行为的认定并不以“事前”或“事后”为标准,当事人的统筹分配收入行为虽然发生在收入入账之后,但是其本质仍然是对协议全体成员的业务收入按照一定比例人为地进行重新分割,也就是对全体成员市场份额的重新划分。与直接划分市场份额相比,这种行为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产生的效果比直接划分市场份额更为恶劣。由于业务收入的划分在后,所以原本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较多收入的经营者的经营成果被人为剥夺了,这对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积极性的打击更大,对市场竞争产生的负面作用更为强烈。
当事人行为具有限制、排除竞争的效果
在正常的市场竞争的状态下,经营者所取得的收入应当与其经营的业务情况成正比,这是激励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的直接动机。经营者的业务越多,取得的收入越多,每个经营者通过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争取更多的客户,追求更高的收入,整个市场也因此而实现优胜劣汰,这是市场竞争的一般规律。
本案中,涉案的25家会计师事务所均为临沂市当地审计、验资等相关会计业务的经营者,相互之间具有明显的竞争关系,理应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获得各自的收入。当事人协议对全体成员单位的收入按照一定指标进行重新分配的行为,事实上是在当事人之间人为进行市场份额的划分,这种行为扭曲了正常市场竞争状态下的收入分配机制,导致了多劳而不多得,少劳却可以获得补偿的不正常状况,挫伤了经营者的积极性,弱化了经营者为争取消费者而不断提升质量和服务的动力,限制了经营者彼此之间的竞争,阻碍了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降低了市场的运行效率。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无论是从行为本身的性质还是从行为产生的限制、排除竞争后果来看,山东省工商局认定当事人的行为构成“划分销售市场”的垄断协议行为都是定性准确,于法有据的。行政复议决定和法院判决也支持了山东省工商局的认定结论。对于垄断案件行为的认定,不能拘泥于法条的文字含义,而是需要综合违法行为的性质及后果进行整体分析。
此外,本案历经两次复议、六次诉讼,虽然当事人的救济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不过同时也带来了行政和司法资源的极大消耗。从行政复议和诉讼衔接的角度考虑,对于垄断协议案件中的多名当事人,是否有必要从制度上视为同一当事人,统一行使救济权,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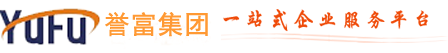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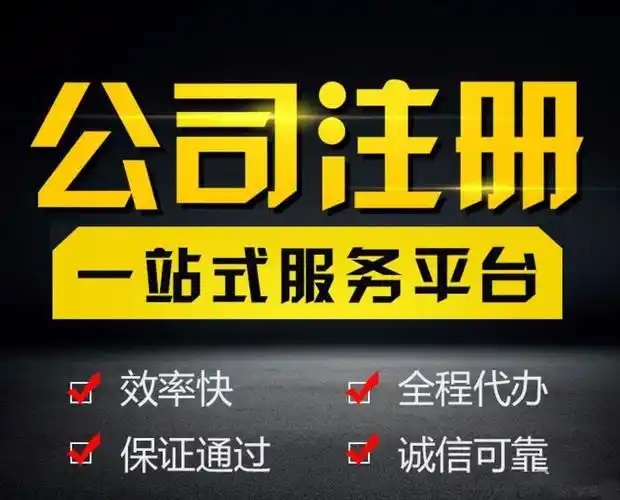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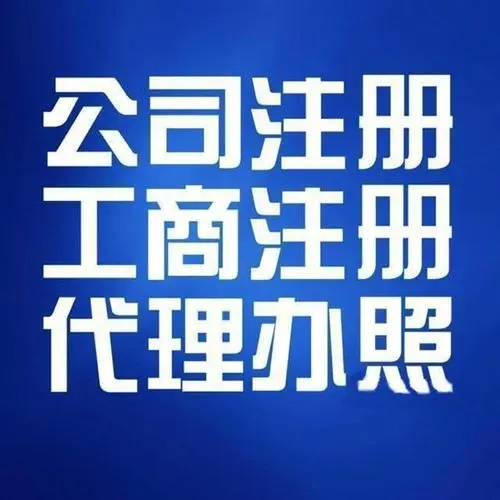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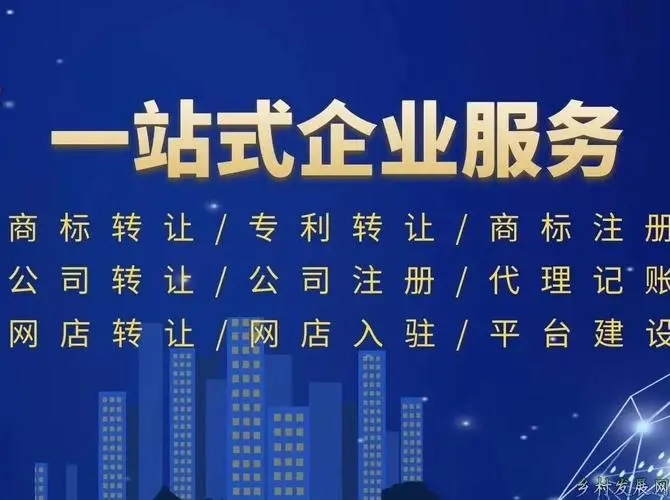
 热门文章
热门文章
